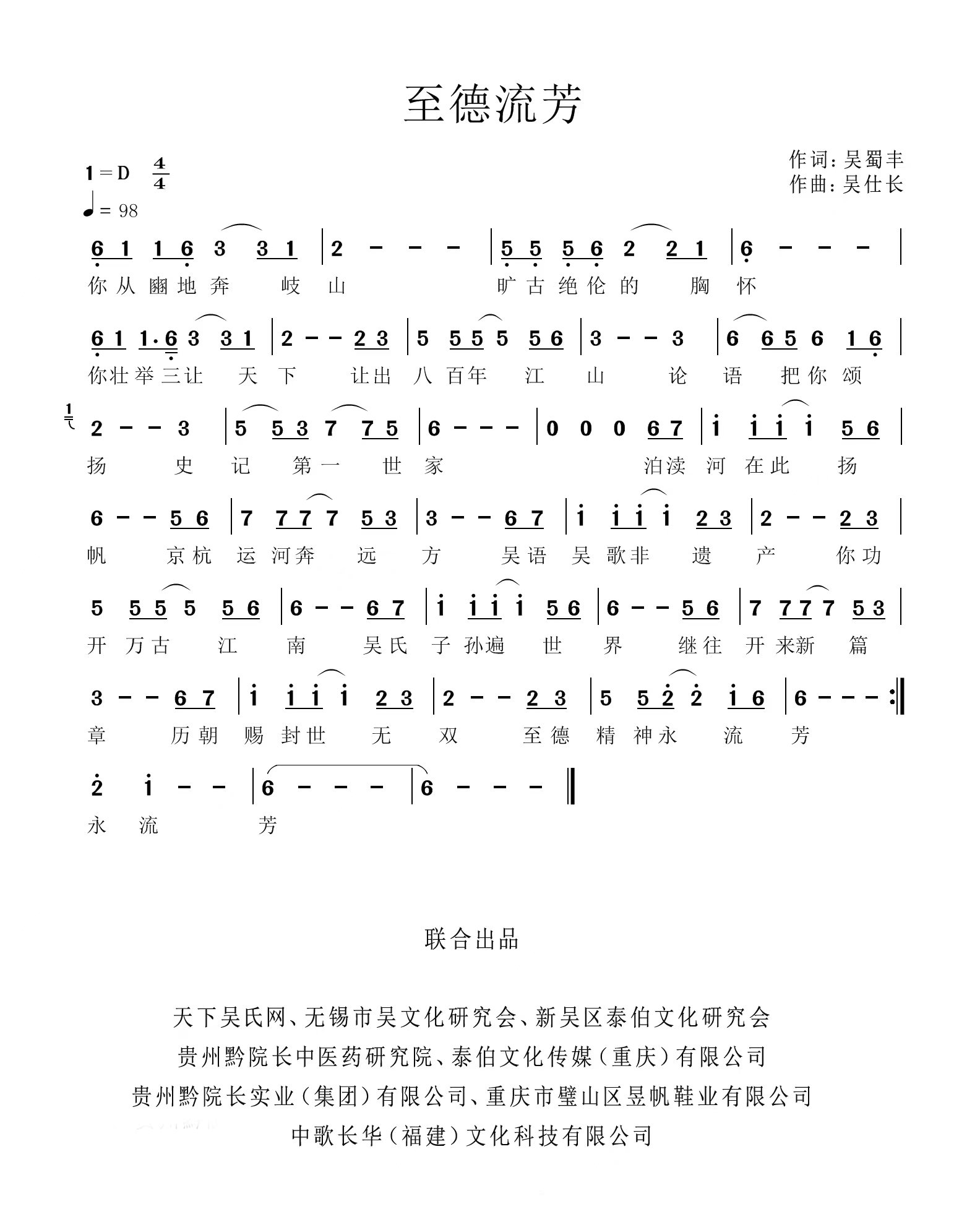文/吴择鹏
2017年3月中旬,承蒙吴因平宗长盛情相邀,我与几位同族友人欣然同赴建德大洋镇一游。早闻大洋镇依兰江而建,既有山水滋养的灵秀之姿,又藏岁月沉淀的人文之韵,此行正为亲身体味这份独有的风情。
论及自然景致,大洋镇最负盛名的当属江东绿道——这条被誉为“杭州最美绿道”的景观带,北起麻车大桥,南至上徐自然村。4.6公里的路程中,一侧是兰江碧水悠悠,波光随微风轻漾;另一侧是田园舒展、村落错落,江东湿地公园的葱郁绿意,与“脆肉雪柚”采摘园的鲜活生机相映成趣,人行其间,宛若步入画中。此外,镇内的浙西第一大峡谷更显奇绝:谷中奇石嶙峋、山泉潺潺,瀑布自崖间奔涌而下,溅起碎玉般的水花,伴着山间草木的清冽香气,满是自然野趣。
而人文底蕴,则藏在那些历经时光打磨的建筑与遗迹里。童氏宗祠古朴庄重,清道光年间的石库门与马头墙至今完好,作为中共建德县委的诞生地,一砖一瓦都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;明初刘伯温题写的琪坪山石刻,字迹虽经风雨侵蚀,却依旧风骨不减;明代东岳庙的飞檐翘角、清嘉庆年间青云桥的石拱弧度,每一处都与山水相融,为大洋镇添了几分历史的深邃。
同行者皆是本家挚友:萧皇塘的吴建华,是义乌小有名气的青年书法家,笔墨间自有灵动气韵;前洪的吴济英,年纪轻轻已是手艺精湛的工艺雕刻师,对古建细节颇有研究;还有寺西的吴宗如,身为土木工程监理,审视建筑的眼光格外专业。我们四人从上溪出发,驶过仇宅隧道,穿过幽暗的洞体便到了兰溪横溪镇,再行一程,全程1个半小时车程,终抵大洋镇。
三月虽属春季,正午的阳光却已带了几分燥热。因平宗长的项目工程部就设在兰江边,离镇上的集贸市场极近。那市场是典型的城乡集市,热闹非凡:新鲜蔬菜还沾着晨露,时令水果堆得像小山,活鸡家禽在笼中扑腾,肉食摊上的鲜肉色泽鲜亮,吆喝声、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,满是人间烟火气。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水产品摊位——毕竟临着兰江,江鲜格外丰富:草虾通体青亮,在盆里蹦跳不止;兰山白条鱼身细长,银鳞泛着光泽,是当地最鲜的河鲜之一;黄鳝蜷在清水中,还有体型肥硕的大翘嘴,鱼鳍展开时格外精神,一看便知是刚从江里捕捞上来的。
因平宗长与嫂子怕我们几个“蹭吃蹭喝”的小兄弟不尽兴,特意买了满满一兜食材:鲜嫩的时蔬、紧实的肉类,还挑了几条最大最鲜活的兰江白条。一想到中午能尝到这江鲜的原汁原味,我们几人早已按捺不住期待
早上八点左右,我们一行三人再次走进高垣村。村里的广场很有特点,有禁毒和孝德两个主题。禁毒广场是建德第一个这类主题广场,孝德广场上贴着村里人行孝的照片;旁边那栋米黄色的“乡村大礼堂农民俱乐部”,平时镇里、村里的文化活动常在这里办。
民居风格不一样,有些挨着古建筑,比如滋德堂古祠堂周围,住的都是同家族的人,院落间有回廊连着,下雨天串门不用打伞,房子的墙砖多是水磨砖,还带精致的砖雕。另外还有新修的下山移民安置楼,样式统一,看着也整齐。村子靠着山、临着水,环境挺好。
村办公楼在广场北边,楼两侧有宣传窗,周围插着些小彩旗,好像刚办过什么庆典。走进楼里,传达室、书记室、妇联、民兵相关的房间,还有便民调解中心都有。没想到一个村的办公楼,跟政府部门似的,该有的都有,挺齐全。
首先接待我们的是高垣村的文书。她肤色白皙,一双大眼睛忽闪灵动,齐整的刘海衬得面容格外清秀,高挺的鼻梁更添几分雅致,周身透着文静优雅的气质。她引着我们三人走进文书室,一边娴熟地泡茶,一边笑着说:“老书记特意交代了,今天有贵客来。”话音刚落,一位六十开外的老者便健步走来,开口便是亲切的招呼:“本家兄弟们,早上好啊!”“宗长好!”我连忙应声。文书这时介绍,这位便是从大洋镇退休的吴福和老书记。
福和老书记精神头十足,上身穿着一件洗得微微泛黄的白衬衫,头戴遮阳帽,手里还握着一把折扇。若添上三缕长髯,活脱脱就是位神采奕奕的“诸葛亮”,眉眼间满是矍铄之气。
几句家长里短的寒暄过后,我们转入正题。我问道:“请问,咱们高垣吴氏是从义乌艮溪迁徙而来的,不知艮溪大致在哪个方位?迁徙发生在哪个朝代?始迁祖的名讳,您这边有记载吗?”福和老书记闻言微微皱眉,沉吟片刻后,缓缓将一段尘封多年的家族往事,向我们娓娓道来。建德大洋镇高垣村与百节桥之间,流传着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渊源故事。
元延佑年间(1314—1320),义乌艮溪人吴铭三,挑着一担绿豆,踏上了四处漂泊的路。他先到绍兴,再往杭州,之后便逆着钱塘江一路向上。途中,他偶遇一位道士,道士给他指了一条安身立命的明路:“你沿钱塘江继续上行,若见到青山如龙盘腾、溪上横卧百节桥的地方,便是你的归宿。”
后来,吴铭三行至如今大洋镇的乌淇头,渡江到对岸的麻车埠,又一路向西探寻。走着走着,他忽见东西两座青山形似青龙,相互回护,气势非凡;低头一看,自己正站在一座用三根棕榈树拼接而成的简易小桥上。他恍然大悟:这不就是道士口中的“百节桥”吗?
欣喜之下,吴铭三在山间燃起一堆火,待次日用石块将火堆围起、覆上泥土作了记号,便匆匆返回义乌老家。他将此番奇遇告知父亲,得到了父亲的支持。于是,吴铭三再次回到这片让他心动的土地,在那堆火的旧址旁搭起一间茅屋,就此定居下来。
他最初居住的地方名叫“吴巡坞”,后因四周山势如龙盘绕,改称“盘龙村”;又因群山环抱如垣墙拱卫,最终定名为“高垣村”。吴铭三也因此成为高垣吴氏的始迁祖,自他之后,高垣吴氏在此开枝散叶,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望族。
只可惜,岁月流转,年代久远,家族谱牒早已散失,知晓先祖往事的长辈也相继离世。如今的高垣吴氏后人,仅知始迁祖铭三公来自义乌艮溪,关于先祖更多的过往,便只剩下一份深藏心底的追思与怀念了。
接着问道:“高垣吴氏留存下这么多古建筑,青砖黛瓦间尽显恢宏气派。高垣村人能有这般光景,想必家境非富即贵,若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做支撑,实在难以想象。”福和书记听后笑了笑,眉眼间似掠过一丝藏着秘密的神色,随即给我们讲起了一段关于宝藏挖掘的传奇往事。
高垣村的发家宝藏,本身就是一段传奇。传说当年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征战天下时,曾积攒下大批财宝,并就地埋藏,兰江两岸的高垣一带便是其中一处藏宝之地。刘伯温还绘制了两张藏宝图:一张用盐卤水墨绘制,交给了朱元璋;另一张则以普通水墨成画,自己留存。只是岁月流转,朱元璋手中的那一张渐渐变得模糊不清。可惜的是,朱元璋与刘伯温在世时,都没能来得及取出这批宝藏。直到明永乐年间,刘伯温的后人才开始四处寻访,想要找到这批遗物。
有一次,刘伯温的后人手持藏宝图,沿兰江逆水而行。同行的船只上,恰好有一位高垣吴氏族人,偶然偷看到了藏宝图的内容。这位族人上岸后,立刻急匆匆赶回高垣村,敲起铜锣召集村民,一同前往青龙山后的破窑挖宝。众人在距窑前台阶十步远的地方往下挖掘,果然发现了用砖头封死的窑门。撬开窑门后,里面竟满是黄金!村民们有序地挖掘宝藏,最后将金子平分,高垣村也因此一夜暴富。
听完老书记讲述的百节桥与宝藏的故事,我们既为高垣村的过往感到欣喜,也越发觉得肩上的担子沉重。这时,老书记又提及一段“无谱源、断脉络”的家族族谱,语气里满是遗憾与急切。他神情凝重起来,对着我们深深作揖,恳切地说:“你们三位是义乌吴文化研究会的成员,对义乌吴氏谱源的研究向来深入,拜托了!拜托你们!一定要帮我们高垣吴氏了却这桩延续百年的寻祖心愿啊!”
尽管目前掌握的信息稀少,寻祖之路必定困难重重,但我还是郑重地回应:“我们一定尽力!尽力而为!”我笑着婉拒了福和老书记留我吃午饭的盛情——嫂子今早出门前特意叮嘱过,一定要回家吃晌饭,说要给我们做几道馋人的菜:喷香的霉干菜蒸肉末、油润够味的牛肉豆瓣酱,还有那腌得咸香透骨的咸猪脸,光是想想,舌尖都忍不住泛出馋意。
大洋当地处理猪头很是细致,会仔细分割成猪舌、猪脸和肥膘肉。那会儿的猪脸是论个卖的,一块二三斤重的,只要十块钱。可谁都清楚,那几年的猪肉价格简直贵得离谱,稍微像样点的鲜肉,一斤就要三十多块。肉荒的影子悄悄笼住了日子,后来才知道,那竟是灾年的征兆——果不其然,第二年全国就遭遇了新冠病毒感染。如今几年过去,回想起来,心里依旧有些发怵,这便是后话了。
午饭后,嫂子还贴心地给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。这般算来,此次大洋高垣之行,不仅饱了口福,还得了心意,真是满载而归。只是,要为高垣吴氏寻回祖源脉络,这又何尝不是一项艰巨无比的任务呢?
吴宗如在因平哥的码头边搭好了临时简易房,诸事妥当后,我们一行四人便同车返回义乌。车厢里的热门话题,自始至终离不开高垣吴氏的祖源探寻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七嘴八舌地梳理着线索:祠堂简介里提及的“艮溪”,石匠师傅口中念叨的“前山”,还有福和老书记绘声绘色讲起的百节桥与宝藏的故事……零碎的信息在脑海里打转,却始终理不出一条清晰的头绪,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几分焦灼。
就在这时,同行的青年书法家、副会长吴建华突然一拍大腿,眼中闪过一丝灵光,开口说道:“哎!我们萧皇塘村前就有一条河,名字正好叫‘艮溪’!它发源于金华兰溪,是从西南往东北方向流的。”
我立刻接过话头:“这就对了!八卦里的东北方对应‘艮卦’,古人给这条河取名‘艮溪’,真是又贴切又有讲究。”建华点点头,继续补充细节:“这条溪水一路往下,从山间飞泄而出,穿过层层密林,漫过仇宅的高地,又绕着萧皇塘的伏虎岩蜿蜒前行。几十里的路程,溪水潺潺不断,最终先流入三板桥的前山村,过了前山村再往前行,就到了沿华村;而穿过沿华村后,它便汇入了潜溪。”
话音落下,车厢里瞬间安静下来——之前困扰我们的“艮溪”“前山”两个地名,竟就这么清晰地“呼之欲出”,与高垣吴氏的线索稳稳对上了。建华又带着些感慨说:“只是现在知道‘艮溪’的人太少了。小山村的古溪名,早就没多少人记得,哪怕去地名办查询,也找不到‘艮溪’这两个字的记录。如今还能说出这名字的,只剩那些土生土长在艮溪两岸的老人,全凭一代代口耳相传的记忆留存着。”
谁也没想到,这桩看似毫无头绪的“无头公案”,竟被建华这几句话点破,寻祖的路一下子有了明确线索——不仅找到了“艮溪”,连“前山”的具体位置也对应上了。至于高垣当地的“前山”,我们猜测,或许是先辈们为了不忘祖源,特意沿用了故乡的地名,以此寄托对故土的纪念与牵挂。
返程义乌的途中,车子恰好经过仇宅隧道,我们特意绕路去了萧皇塘。刚到村口,就见一条溪水从村前缓缓流过,吴建华指着那汪涓涓细流,语气笃定地说:“看,这就是艮溪。它往下游流去,就到了前山村,而且前山村大多姓吴;等淌过沿华村,最终会汇入潜溪。”
一旁的济英难掩激动,声音里满是感慨:“这次高垣寻祖,要是没有建华同行,‘艮溪’‘前山’这两个关键线索,恐怕真要石沉大海了。这份巧合与熟悉,换了谁都替代不了。”众人都深以为然——此前我们只知潜溪,对艮溪的名号毫无耳闻,却不知这两条溪的关联里,还藏着一段不得不说的人文典故。
元末明初被誉为“开国第一文臣”的大文豪宋濂,与如今义乌上溪镇的沿华村(旧称潜溪村),有着一段颇深的渊源。
宋濂的祖籍本是金华潜溪(今浙江金华市金东区傅村镇),后因个人发展与生活变迁迁居至浦江青萝山(今浙江浦江县郑宅镇)。他在《萝山迁居志》中曾明确记载:“余世居金华孝善里之潜溪,其地在县东七十里禅定院侧”,足见金华潜溪是他出生之地,也是他度过人生最初二十年的故土。后来即便迁居浦江,他仍将当地居所命名为“潜溪”,以此寄托对祖籍地的牵挂,不忘根本。
而义乌上溪镇的潜溪村(即沿华村宋氏聚居处),实则是宋濂族裔的落脚地。据《潜溪宋氏宗谱》记载,大约在公元1500年前后,宋濂胞兄的后裔从金华傅村迁徙至此,在沿华村扎根繁衍,才让“潜溪”这一与宋濂相关的名号,在义乌上溪延续下来。
更有意思的是地理与行政的关联:原吴氏聚居的前山村,与沿华村相距不过1公里,称得上是一衣带水的近邻。两条溪流在此串联起过往——从沿华村溯源而上的溪流,便是曾在寻祖中提及的艮溪;自沿华村开始往下的河段,则被称作潜溪。如今,前山村已并入沿华村,统一称作潜溪村,行政上更名为潜溪社区。
这般变迁之下,曾经承载着地名记忆的“艮溪”,终究慢慢淹没在岁月长河里,只在旧闻与族裔的追忆中,还留着些许痕迹。返回义乌后,我第一时间找到时任吴文化研究会会长的吴琅坤,将高垣寻祖的前因后果与关键线索,细细向他作了汇报。(当年我担任吴文化常务副会长)
琅坤会长听罢,难掩震撼,当即拍板决定:下周末就组织人手,深入前山村核查当地谱牒资料,务必查清是否有关于高垣铭三公迁徙的记载。彼时正是暮春,义乌的天气不燥不凉,格外宜人,前山村的景致更是秀丽旖旎。一行人驱车前往,沿途循着溪源、傍着山峦——一条新修的公路依山傍水,从市区过上溪镇直通向桃花坞,穿过几座崭新的隧道后,在沿华村路口下了主路,转入乡间小道,不多时便抵达了三板桥前山村。
此次行动由琅坤会长带队,他虽不精通谱牒知识,同行的组员却都是实打实的“老学究”,个个揣着丰富的谱系研究经验:有来自义亭镇白塘村的吴福兴宗长,德高望重;有桃花坞的“种桃大王”吴根生,还带着他的儿子吴志强——别看志强是个年轻人,研究谱牒已有不少年头,功底扎实;(因根生,志强,琅坤同属椒山吴氏支派而前山也属该支)随行人员还有此前立下功劳的吴建华副会长也在其中;另有柳溪的吴荣连,更是当地有名的资深“谱头”,查谱辨源的本事数一数二。
一行人目标明确,抵达后便径直往前山村村委会办公室走去,只盼着能在那里找到关键的谱牒线索。管理谱册的村民尚在赶集归途,我们已与前山宗长们围坐在办公室的圆桌旁。琅坤先致开场白,逐一向众人介绍吴会组员;轮到书记引荐村中尊长时,吴根生却先一步与几位尊长握了手——原来他们同属椒山支派,村庄相邻本就熟络,再加上吴根生一手嫁接桃苗的好手艺,邻近三村常请他上门指导,人脉广、熟人多,寒暄间便聊起了农事稼穑。
待介绍到一位前山宗长,他笑着自报家门:“痴长八十有三,在村里辈份最大,一辈子就靠耕种过活。年轻时家里穷,没读过书,便让四弟去读书了。他现在是义乌市恒大公司的总经理兼党委书记,之前还当过义乌市小商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。所以村里人都喊我一声吴老大。”话音落,满座掌声响起,吴老大随即伸出那双青筋虬结、布满老茧的手,与在场人一一相握。
我见状立刻上前,恭敬地问道:“吴老大伯伯,您老好!想跟您打听个事——咱们前山村的祖上,有没有一位叫吴铭三的先人,后来迁徙到了建德大洋高垣村?”吴老大闻言略一沉吟,随即眼神亮了亮,语气肯定地答道:“有!当然有!”
这两个字像石子投进湖心,我心头瞬间涌起一阵狂喜——悬在高垣村人心中的祖源谜底,终于有了揭开的希望。我按捺住激动,急忙追问:“那您能讲讲铭三公当年迁徙的往事吗?”
“能!怎么不能!”吴老大笑着点头,声音里带着几分对旧事的珍视,“这是我们前山人代代都知道的陈年旧事,祖上一直口口相传着这个故事呢……”暮春的山风恰好从窗外徐徐吹过,带着草木的清香,轻轻拂过在场每个人的脸颊,也吹得吴会众人的心,都暖洋洋、醉醺醺的。
吴老大虽是目不识丁的粗人,却藏着一身说书的好本事,讲起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来,人物鲜活、情节生动,更别提自家祖上的旧事了。众人听得心痒难耐,纷纷鼓掌起哄:“讲讲吧!快讲讲!”
故事要从元末明初说起。前山吴氏的始祖寿卿公,娶妻王氏,膝下育有三子。长子铭一留居前山,延续本支血脉;次子铭二迁居金华洪源,后世称“凤山吴氏”;而三子铭三,便是这段往事的核心主角。他自小聪明伶俐,念过几年私塾,长大后更是秉持勤劳节俭的性子,日子过得踏实本分。
一日,铭三挑着一担柴到吴店市口售卖。卖完柴后,手里攥着几两刚赚的碎银,在集市上漫无目的地闲逛,恰巧撞见一位摆摊的看相先生。他摩挲着银子犯了难:想请先生看相,问问日后财运如何、何时能时来运转,可手头这点钱实在单薄;可就此转身走开,心里又实在按捺不住那份期待。彼时他肩上还扛着挑柴的扁担,冲尖上缠着束柴的麻索,正站在原地犹豫不决,那看相先生反倒先开了口:“卖柴的小伙,过来吧!看你是穷苦人家,为人老实本分,我便免费送你几句箴言。”
先生示意铭三坐下,细细端详他的面相,缓缓说道:“你且听好——天庭饱满,主子孙荣昌,往后家族人丁兴旺是定数;准头丰隆,有三十年之造化,中年起必有运势加持,能成一番事业;再看你双耳贴脑,正是‘对面不见耳,问是谁家之子主大贵’的贵相,绝非久居人下之人;更难得是地阁方圆,主年高德劭,日后不仅能安享晚年,还能得邻里敬重、子孙孝顺。”
话到此处,先生话锋一转,语气愈发郑重:“你本是员外之命,只是需‘离祖得贵’——离开故土方能得偿所愿,此去定是‘离祖大利’。切记,日后若遇到一处有‘百节桥’的地界,那便是你安生立命的归宿。到了那里,你不仅能发家致富、显贵一方,更能子孙满堂、福禄绵长!”
铭三听得如痴如醉,只觉先生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心坎里,连呼吸都不由得放轻。等他回过神来,满心感激地起身要道谢时,眼前的看相先生却没了踪影。他急得四处张望,集市上依旧人来人往、喧闹如常,可那先生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,再也寻不到踪迹。
铭三站在原地,反复念叨着“离祖得贵,离祖大利”,又想起先生说的“百节桥”与“安生立命”,心中忽然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闯劲——或许,是时候放下眼前的安稳,离开家乡,去寻找那座能让自己扎根、让家族兴旺的“百节桥”了。
百节桥畔寻祖迹,高垣山水定家根
吴老大的故事正讲到兴头,底下有人忽然笑道:“您这百节桥的说法,倒和高垣那边的传说对上了!”众人追问,他便解释:“虽说一个是贩绿豆谋生,一个是卖柴郎寻路,但‘遇百节桥安身’的内核,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!”
这话勾得吴老大更来了兴致,接着往下讲:“咱们椒山吴氏,大多扎根在大山深处。那里土地贫瘠,田少坡多,单靠种地难以为生。所以农忙时,族人都扎在田里侍弄庄稼;一到农闲,男人们便背着家伙什外出,要么走街串户弹木棉,要么劈棕丝串棕衣,靠这两门手艺换些散钱,贴补家里的油盐酱醋。”
他话锋一转,又落回铭三公身上:“要说这手艺,铭三公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他念过几年私塾,心思细、手又巧,弹的棉花蓬松柔软,串的棕衣结实耐穿,更绝的是在 棉絮上绣花——绣对鸳鸯,仿佛下一秒就要戏水;绣个红双喜,喜庆劲儿能透出来;绣上‘吉祥如意’的纹样,更是家家户户都抢着要。”
凭着这一身好技艺,铭三公背着弹棉花的家当,翻过高高的山梁,走过弯弯的田埂,不知走了多少路,也不知问了多少人,冥冥中竟走到了建德大洋的高垣村。一进高垣地界,他便被眼前的风光绊住了脚:远处青山层叠,像被墨染过似的,云雾绕在山尖,似纱似带;山脚下是连片的梯田,田埂蜿蜒如银链,若是农忙时节,定是满田的绿意;近处溪水潺潺,清得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,溪上竟架着一座特别的桥——不是砖石垒的,也不是木头铺的,而是用三根粗壮的棕榈树干并排搭成,树干上的节疤清清楚楚,远远望去,倒真像“百节相连”,当地人都叫它“百节桥”。
看到这桥的瞬间,铭三公猛地怔住了——当年看相先生的话突然在耳边响起:“日后若遇到有百节桥的地界,就是你安生立命之地!”他站在溪边,望着潺潺流水与“百节桥”,又看了看四周青山环绕、炊烟袅袅的景象,心中忽然落了定:这就是他要找的地方,是能让他扎根、让子孙繁衍的发祥地!
就在吴老大讲得唾沫横飞,众人听得入迷时,人群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赶集市的谱牒管理员满头大汗地跑回来,一进门就双手抱拳作揖,连连道歉:“对不住!对不住各位!接了书记的临时通知时,我都快到上溪了,紧赶慢赶才回来,让大家久等了!”
椒山吴氏老谱,是名副其实的家族“厚重家底”——三箱共48部,堆叠起来便见分量,这庞大体量背后,是椒山支派占义乌吴姓三分之一强的人丁兴旺,也衬得“义乌吴氏八万之众、位列前三”的说法愈发真切。
当管理员搬出沉甸甸的谱箱时,老学究吴福兴先生提议焚香三支,那一刻,周遭的空气仿佛都静了下来。香火燃起的轻烟里,“祭告祖宗,今日请谱寻游子,保全族平安”的话语落进耳中,忽然就生出一种敬畏:这不是普通的查资料,是隔着时光与先祖对话,是替散落的族人找回家的根脉。
大家都知道祖上口耳相传的旧事,可“活证”之外,总盼着文字记载来给这份念想一个实落。世序、朝代、年代,缺了哪一样,家族的脉络就断了层,这份对“史实佐证”的执念,大概是每个寻根人心里最紧的弦。
面对这浩如烟海的谱牒,我和福兴先生起初也犯了难:48本逐本查,三天三夜恐怕都摸不着头绪。直到我提议“先查世系五线谱,再查行传”,他一拍大腿说“此法甚好”,悬着的心才落了一半——找对了门路,才算不辜负这一箱箱老谱。
随后,我与福兴、荣连三人净手净意,轻轻从樟木箱里取出老谱。指尖触到略微发黄的纸页时,竟有些紧张:怕碰坏了这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物件。好在纸张不霉不蛀,保存得完好,再看扉页上“《椒山吴氏宗谱》”几个大字,醒目又庄重,忽然就红了眼眶——这哪里是纸,分明是家族的魂,是一代代人想护住、想传下的念想啊。
老谱的排布从不是随意堆叠,而是循着严谨的章法,一页一页都藏着家族传承的深意。单说开篇,便先以“谱名”立住根基——像《椒山吴氏宗谱》,“椒山”二字既是扎根的地名,更是这支吴氏的身份烙印,一提起便知是哪一脉族人;“吴氏”明姓氏,是血脉的标识;“宗谱”二字分量最重,不是简单的名录,而是列祖列宗的生平脉络、家族故事的合集,翻开它,就像翻开了一部家族专属的传记。
紧接着是“新谱序”,多由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者执笔,字字皆是心意。内容分作三部分:先是追本溯源,把支派的历史沿革、世系从哪里来、如何迁徙繁衍说清楚,让后人知道自己的根在何处;再是点明修谱的意义,不是为了好看的册页,是为了把血脉连起来,把家训传下去,免得日子久了,族人忘了来路;最后总要写几句对族里的期许,盼着子孙安居乐业、日子越过越富裕,也盼着家族能一代代兴旺下去,这份念想,字字都暖。
之后便是“历代老谱序”,这可是老谱里的“珍宝”。不少序文出自过去的名人之手,或是族中先辈留下的笔墨,一页页读下来,能看到不同年代里,先辈们对家族的牵挂——有的写当年修谱的不易,有的记家族曾经历的风雨,这些文字像桥梁,把不同时代的族人连在了一起,让人知道,我们今日珍视的家谱,早有一代代人用心守护过。
再往下翻,是“凡例”,这可不是枯燥的规矩,是这一次修谱的“乡规民约”。哪些人该入谱、哪些事该记载、世系该怎么排、文字该怎么写,都写得明明白白。看似严苛,实则是为了让家谱更真实、更规整,免得后人查谱时乱了头绪,这份细致,藏着先辈对家族传承的郑重。
要等到第六项,才轮到“世系”——就是之前我们想查的世系五线谱。它像家族的“血脉地图”,一辈辈人的名字、辈分、亲缘关系都清晰列着,顺着这一页页看,能清楚地看到家族从哪一代传下来,谁是祖辈、谁是宗亲,再也不会错了脉络。
其实一部完整的老谱,远不止这几项,拢共算下来有二十四项之多。除了这些,还有家训、族规,教后人怎么做人、怎么持家;有祠堂记、坟茔图,告诉族人先辈的祭祀之地在何处;有族人的行传,不光记名字,还记着他们的生平、德行,有的是勤恳持家的普通人,有的是为家族争光的贤者,每一个名字背后,都是鲜活的家族故事;甚至还有族产的记载,田亩、房屋如何分配,如何为族里的孤寡提供帮助,处处透着家族的温暖。
这二十四项,哪一项都不能少。合在一起,不只是一本本纸页,是家族的历史书、家训集,是血脉的证明,更是后人能触摸到的先辈温度——知道了这些,再翻老谱时,指尖触到的就不只是发黄的纸,更是一代代族人用心攒下的家族记忆。
谱间烟火:一碗泡面也香甜终于翻到第四部老谱,心心念念的线谱图表赫然在目,指尖刚触到那规整的线条,办公室外的声响就渐渐涌了进来——原是午饭时间到了,隔壁乡村康养中心的人听说我们在查老谱、帮高垣寻祖,都好奇地围过来,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,倒让这寻谱的氛围添了几分热闹。
海波书记见状,连忙笑着招呼:“本家兄弟们,走,我请大家吃个便饭!”又怕我们介意,补充道,“村里小,就三百来口人,没饭店,只有家代销店,我带你们去吴店街上吃。”
这话刚落,琅坤会长就摆了摆手:“去吴店往返路远,太费时间了!咱们抓紧查谱才是要紧事,不如就在代销店买几包方便面,对付一口就行。”海波书记一听就急了,脸露难色:“那可不成!哪能让你们吃这个?咱前山村再小,待客的规矩不能少。”可建华、福兴他们也跟着劝,说等认祖归宗真成了,再好好搓一顿也不迟,现在节省时间最关键。海波书记拗不过众人,只好点头:“那我去买!”
他话音还没落地,吴志强父子就拎着一大包方便面走了进来,管理员也赶紧端着开水过来,一脸歉意地说:“委屈大家了。”
肚子早饿得咕咕叫,我拆开两桶面,热水一冲,香味瞬间漫了开来。平时我最不爱吃方便面,可今天不一样——线谱图表有了眉目,寻祖的路好像一下子近了,胜利在望的欢喜劲儿揣在心里,连这简单的泡面都变得格外香。几口下去,浑身都暖了,只想赶紧吃完,再接着去谱页里找那关键的线索。
谱间烟火:一碗泡面也香甜
终于翻到第四部老谱,心心念念的线谱图表赫然在目,指尖刚触到那规整的线条,办公室外的声响就渐渐涌了进来——原是午饭时间到了,隔壁乡村康养中心的人听说我们在查老谱、帮高垣寻祖,都好奇地围过来,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,倒让这寻谱的氛围添了几分热闹。
海波书记见状,连忙笑着招呼:“本家兄弟们,走,我请大家吃个便饭!”又怕我们介意,补充道,“村里小,就三百来口人,没饭店,只有家代销店,我带你们去吴店街上吃。”
这话刚落,琅坤会长就摆了摆手:“去吴店往返路远,太费时间了!咱们抓紧查谱才是要紧事,不如就在代销店买几包方便面,对付一口就行。”海波书记一听就急了,脸露难色:“那可不成!哪能让你们吃这个?咱前山村再小,待客的规矩不能少。”可建华、福兴他们也跟着劝,说等认祖归宗真成了,再好好搓一顿也不迟,现在节省时间最关键。海波书记拗不过众人,只好点头:“那我去买!”
他话音还没落地,吴志强父子就拎着一大包方便面走了进来,管理员也赶紧端着开水过来,一脸歉意地说:“委屈大家了。”肚子早饿得咕咕叫,我拆开两桶面,热水一冲,香味瞬间漫了开来。平时我最不爱吃方便面,可今天不一样——线谱图表有了眉目,寻祖的路好像一下子近了,胜利在望的欢喜劲儿揣在心里,连这简单的泡面都变得格外香。几口下去,浑身都暖了,只想赶紧吃完,再接着去谱页里找那关键的线索。
暮春的山裹着温润的绿,夕阳把金辉漫上去——近山的深碧叶尖沾着暖光,山腰残存的几簇杜鹃被染得更艳,连松枝的墨绿都泛着柔润。风掠过时,叶影晃着碎金,远山叠着淡绿与浅蓝,渐渐融在渐暗的天色里,只剩余晖漫在山尖,温得像化了的糖。
可此刻,这山间夕照的暖,远不及我心中的滚烫。近百年的寻祖梦,竟在这一刻成真!高垣村终于能归宗认祖,这份激动攥得人心尖发颤。水有源,树有根,寻根问祖从不是空泛的执念,是刻在民族骨血里的传统,是不忘来路的美德,更是对列祖列宗最深的告慰。
小山村已亮起零星灯火,村民们热情得不行,拉着要留我们吃饭。我们连连婉拒——肚子确实饿得咕咕叫,可那份寻到根的甜,早把饥饿压了下去,这份滋味,外人怎会懂?
正沉浸在这份圆满里,手机突然响了,是老婆的声音,带着熟悉的温软:“快回家吃饭,饭菜都要凉了!”没有多余的话,却像一股暖流裹住心口。山间的余晖再暖,也抵不过这一句寻常叮嘱里的牵挂,原来最踏实的幸福,一边是寻到的千年祖根,一边是等你归家的人间烟火。
《高垣行字母》原→相→圣造→ 尧→湛→質→若山→吴福→伯→千→衍→寿→铭三→进→嵩→升→富→永→景→志→仁→义→忠→信→文→章→礼→乐→孝→友→贤→良→宽→和→慈→惠→诚→正→修→齐→端→莊→宁→静。注:吴福公尊为椒山吴氏始迁祖,其五世孙行潘府君,讳寿卿,迁居前山艮溪。
寿卿公之三子行铭三,讳錄观,(外世纪泰伯91世,内世纪吴福6世孙)由椒山吴氏前山村迁徙睦州建邑吴巡坞(今高垣),迁徙朝代为元末明初,年代为元延佑年间(1314一1320)铭三公之世序、迁徙朝代、及年代三者相符,证据链确凿。
附诗二首
《七律》- 艮溪
潺潺清澈九曲溪,
源自东北金兰义。
径流萧皇伏虎山,
高嶺仇宅湿马蹄。
龙飞艮溪三板桥,
凤舞前山延陵里。
凌波直泄姑塘下,
川逼沿华入潜溪
清澈见底,潺潺艮溪,源头发自金华,兰溪。流淌义乌。流径萧皇伏虎山下,穿过仇宅高嶺,盘龙钱三寺前,凌波三板桥下,九曲环抱前山风水宝地。径直流过姑塘下,威逼沿华流入潜溪。艮溪千年流淌,径流不息。
延陵散人吟於戊戍年夏日
西江月·艮溪怀古
西南翠峦凝黛,
遥观峻岭含青。
忽逢壑雾瀑奔倾,
惊起林深鹿鸣。
潭谧涧波悠悠,
婺川向东北行。
艮溪三叠注潜汀,
潜溪怀古低吟。
艮溪发源于金婺兰溪,一路自西南向东北,穿峰越岭,途经仇宅、萧塘伏虎书院,直逼三板桥、沿华溪口,最终汇入宋濂故居旁的潜溪。悠悠数十里艮溪,历经千年依旧奔腾不息。宋濂号潜溪,其才情与风骨为后世敬仰。遥想昔日宋濂先生於两溪之畔,低吟浅唱,经久不绝。
延陵散人吟唱乙巳己卯仲春
【关于我们】今日采访.com、天下吴氏网、至德传媒网隶属于泰伯文化传媒(重庆)有限公司独家运营的三网合一公益性网站,集官网、APP、自媒体、抖音、视频号、公众号同步传播的综合性融媒体平台。
在国家法律许可下,遵纪守法、守正创新、传递正能量,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,坚持客观、真实展播、记录生活,坚持正确的主观立场,以弘扬至德精神!传播优秀文化为主旋律!
渝ICP备 15011658号-3天下吴氏网
渝ICP备 15011658号-5至德传媒网
渝ICP备 15011658号-8今日采访.com
只要你是正能量的来稿,我们都欢迎!
联系人 吴蜀丰
电话 18883313913(微信同号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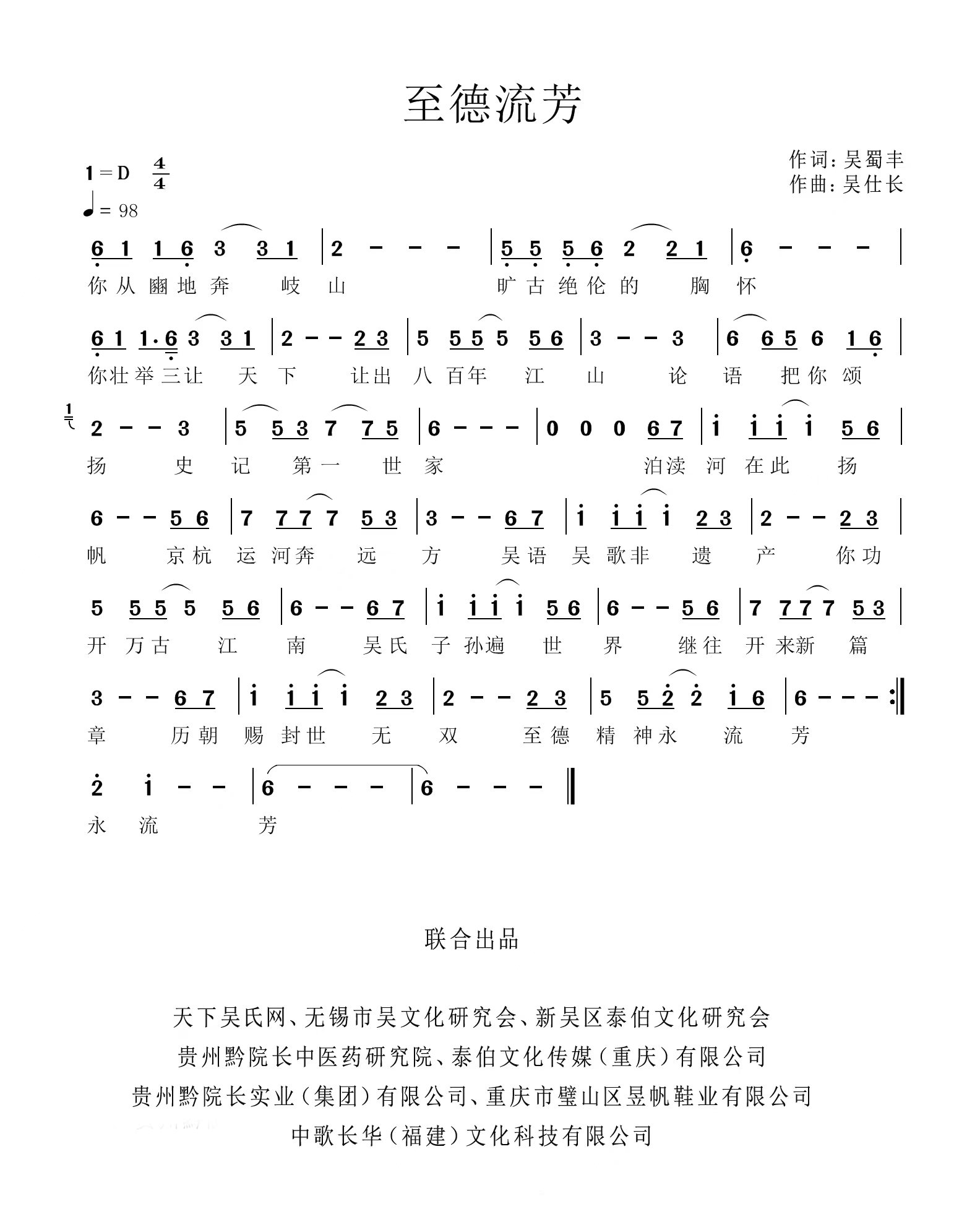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吴蜀丰